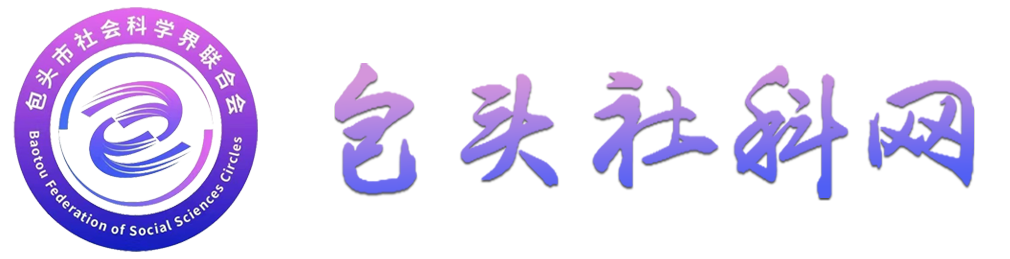在西方史学的主流叙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通常界定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处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彼时已经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然而,长期以来国外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甚至避而不谈。因此,有必要深刻认识中国战场的重要历史地位。审视国际秩序的演变,可以为理解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诉诸一战后维护国际秩序的组织——国际联盟寻求解决。国联于1931年12月10日决议组建调查团前往东亚调查。在调查期间,国联调查团收到中国民众数千封说帖,说帖内容揭示了民众抗日事实——“到处抵抗日军”,“三省人民抗日救国之精神与反对伪国之决心”,“各处的义勇军群起抵抗日本惨无人道的军队”,“誓死反对并与决斗到底”。
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清晰认识到日本对华侵略的本质,这充分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系列声明中。193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鼓励“民众自动组织北上决死团到东北义勇军中去,收复东三省失地……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0月7日,中共中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强盗侵略是战争发展中的重要的阶段”。
除宣传动员外,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开展反日宣传、工人罢工、农民抗租抗捐等运动。从1932年春到1934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18支抗日游击队。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组织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成为局部抗战时期东北战场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主导国英法采取绥靖政策,美国亦未能遏制日本侵略,不仅导致中国实际上独自承受日本侵略与抗日压力,而且纵容了日本侵华行径。在国联不认可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后,日本断然退出国联,逐步扩大侵华战争。从国联视角审视,可以明确中国战场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独自承担抗击日本侵略的重担。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空前严峻的抗日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将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联。随着日本侵略行径的野蛮性与中国军民抵抗的英勇性渐为世人所知,国联从道义层面支持中国并谴责日本。1937年9月27日,国联大会下属远东咨询委员会通过谴责日本空袭的决议。10月6日,国联建议成员国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后的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国际社会仅在口头上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致使日本侵略扩张更加肆无忌惮。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国民政府又一次向国联提出申诉,呼吁援助中国,国联理事会宣布各会员国可以实施对日制裁。日本则以更激烈的对抗回应,宣布决定终止自退出国联以来与国联各机构一直保持的合作关系。
中国战场的抵抗事迹与战略贡献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英国国际联盟协会会刊《前进》(Headway)对此有诸多记载。1938年6月,《前进》刊文强调“无论战局最终走向如何,中国已然击碎所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意义之深远,实不亚于战场上的任何捷报”。1940年3月,田伯烈在《前进》刊文,警示不能因为欧战忽视抗日战争,“当欧洲战场的危急事件牵动世人目光时,我们极易遗忘……中国以非凡勇气与坚定意志抗击侵略的战争”。1942年9月,《前进》刊文明确指出,“中国实为那场引爆二战之侵略暴行的首位受难者。即便不计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战历时亦近其他盟国两倍”。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联名存实亡,国际秩序亟须重构,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得以确立。
鉴于国联所维系的国际秩序未能有效遏制日本侵略,中国早已萌发关于新国际秩序的讨论,东方主战场成为孕育新国际秩序的沃土。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提出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概念,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其中,“世界的统一战线”理念蕴含着新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共中央强调:“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舆论亦掀起关于新国际组织构想的热议,从“国联重组”到“新的国联”,各献其策。
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战略贡献,奠定了其作为新国际秩序核心成员的地位。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其整体军事战略受到多重掣肘:中国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放弃“北进”计划,苏联得以抽调军队支援莫斯科保卫战;中国的持续抵抗延缓日军“南进”速度,为美英争取备战时间;中国派遣远征军“西向”入缅作战,解救英军和粉碎日德中东会师图谋。正是基于抗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主要筹建者之一。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通过《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标志着四大国共同建立新国际秩序。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核心地位,是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关键因素之一。1944年8—10月,中美英苏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拟定新的国际组织章程。中国代表团积极建言献策,提交《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中美英苏共同草拟出台《国际组织建议案》,确定未来联合国的轮廓。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一致同意战后建立联合国,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奠定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基础。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开幕,中美英苏4个发起国的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6月26日,《联合国宪章》举行签字仪式,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字。
从一战后效能不彰的国际联盟,到二战后更具权威性的联合国,其演变过程深刻蕴含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与东方主战场的战略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诉诸国联,而国联的绥靖政策与对日妥协,使中国在孤立无援下独自抗击日本侵略,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中国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抗战,彰显了中国战场的坚韧性,并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正是中国战场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发挥的关键作用,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并在联合国机制中实现从被援助对象向国际秩序构建者的历史性转变。